文化名人的读书生活
——第27个“世界读书日”专访叶辛、顾久
□本报记者 万里燕 王吟
编者按:
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其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于1995年正式设立,旨在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读书,能够启迪智慧,洗涤心灵,充实人生,在仰望星空浩瀚的同时,也能审视自身的渺小。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和著名学者顾久先生,希望通过他们畅谈自己的读书人生,让广大读者能从中找到阅读的动力和意义。

让书籍常伴你的生活。
——叶辛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曾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花》《海上文坛》等杂志主编。著有多部著作,其中《高高的苗岭》被改编成电影《火娃》全国上映,《蹉跎岁月》《孽债》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国热播。
记者: 1969年至1979年,叶辛先生作为上海知青,在贵州修文插队,十年的时间里,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1969年3月31日,是很多上海知青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一生铭记的日子。在那天,我与一批知青离开上海,前往贵州插队。
当时,虽然知青随身携带的物品不受限制,但在那个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年代,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大家也没多少东西好带。在其中,我的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因为特别重,十分引人注意。4月4号,卡车把我们送到公路边,离最终目的地还有三公里多路。那时候的贵州不像现在的交通这么好,车子进不去,只有靠走。老乡来接我们,帮我们拿行李,很好奇什么东西这么重。到了地方我打开箱子,全是书!老乡就笑着说,这两个箱子最重,还猜你家一定很有钱,原来是个书呆子。
这两箱书是我在离开上海前精心挑选的。那时候我喜欢读小说,选了很多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书,其中最喜欢的是《父与子》和《前夜》,还有泰戈尔的《沉船》,我也非常喜欢。
在插队期间,一有时间,我就读书。当时带的这两箱书,其实在上海的时候都读过,但是每次重温,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萌生了写作的愿望。于是我把这些重温过无数遍的书又细细再读,一行一行的琢磨,这些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比如我读高尔基的《童年》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远在苏联的外国老头,为什么能把他们的生活写的如同让我看到一般。我甚至还拿起一些我喜欢的书,对着太阳照,仿佛文字当中就有写作的密码。那时候我读书,已经不仅仅是“爱”读,而是用“心”去读。通过这样一边读一边思考,我开始觉得写小说这件事并不难。
有一次,一起插队的知青小李借了我的《红与黑》去看,然后他感慨这么厚的一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其实写小说并不难,我也可以试着写写。小李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你写!要什么帮助尽管说!”
小李的父亲是上海南京路上出名的老字号饭店“邵万生”的一个副经理,是他父亲耳濡目染,小李做得一手好菜。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后,他便经常做菜给我吃。后来我们开玩笑的说,读书读书,读得了一个帮我煮菜的好厨子。
我带去的两箱书都是世界名著。其实在我小时候,也只喜欢看《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但是后来读书多了,我自然而然的意识到,好看的书是把我们缤纷多彩的生活都描写出来的书。因此,读书不但让我热爱上了文学,还给我展示出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后来我的小说《孽债》,灵感就是来源于我知青插队的那段岁月。《孽债》被拍成电视剧后,全国各地的知青都给我写信,一下子收到几百上千封来信,把导演办公室都堆得无处下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知青问我怎么知道她的故事的。其实那时候的知青,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所发生的事也大同小异,这就是写作来源于生活的魅力。
记者: 1979年至1989年,叶辛先生在贵阳,担任《山花》杂志主编,这个阶段里,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的,甚至南美洲的翻译作品,包括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涌入中国,这让我看书的选择多了很多。但由于工作的繁忙,我大多时候都选择一些刊物,比如《译林》《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等,还有一些中长篇的小说。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加缪的《鼠疫》,还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概因为之前的环境限制,突然读到描写爱情的小说就特别令人着迷。
在这个时期,我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结出了累累硕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蹉跎岁月》,我在书中刻画了一批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的青年们,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时代号召下,或被感召、或被迫无奈,前仆后继地去往了艰苦的农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找到不一样的青春和人生意义。此书一经出版,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曾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至今,《蹉跎岁月》已出版40年,有23个版本之多。
在我十年的知青生活中,吃了很多苦,也收获了很多。我见证了知青返城的历史,也目睹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山乡巨变。
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集体经济模式,突然要转变到私营经济模式,无疑艰难且痛苦,其过程不亚于一场斗争。
在修文的10年间,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无数贫苦生活的画面,“大呼隆”的生产方式让农业效益越来越差。但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之后,我再次走进山乡时,惊讶地看到,农民的生活好了,多年不见的猪肉,吊在那里随便买,农民顿顿吃起了白米饭,再不用往里掺洋芋和番薯了。所有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全都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乡村带来的变化。于是我就想,命运既然让我亲眼见到了这场巨变,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巨变给乡间带来的崭新气象,我应该写一本新的书,写一写不同的人在这场变革当中的困扰、苦恼、犹豫及新的精神面貌。之后,我花了5年时间写成《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后来,三部曲汇编成《巨澜》,并在去年被编入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
记者: 1990年,也正是改革开放不久,叶辛先生回到上海,回到与贵州完全不同的一片天地之后,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1990年秋,我回到上海,仿佛到了一片和贵州完全不同的天地——上海有很多书都是在贵州无法找到的,于是又开启了我读书生涯中的“拾遗补漏”阶段。
当时辛格有一本书《敌人,一个爱情故事》,我特别想看,在贵州的时候一直在找,但直到我回到上海,才终于找到。那时,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因为时代的原因,对于读书的人来说,当时的贵州和上海几乎是不同维度的世界。所以我回到上海后,就“拾遗补漏”了很多书,包括《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黑色的诱惑》等等。
记者: 叶辛先生选择了读书,而读书也改变了叶辛先生的人生。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您对各位读者有何寄望?
叶辛: 书籍陪伴了我一辈子,读书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读书不仅让我学会了写作,更带我领略到了丰富精彩的世界。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想对所有人说:读书可以充实你的人生,使你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使你的眼界更开阔,使你看待事情的视野更高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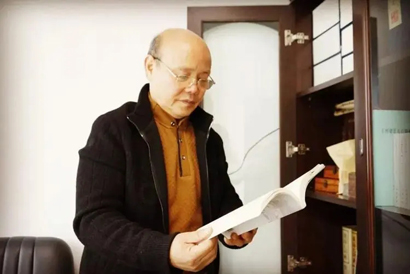
读书像开窗户,能让没有窗户的茅屋变成宫殿;读书像长翅膀,能将人举上没有阴霾的丽日蓝天。
——顾久
顾久,1951年9月出生于贵州贵阳。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贵州省文联原主席、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贵州文库》总纂。
记者: 电子阅读当道的今天,纸质书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您的读书生活中,对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如何理解?在有限的读书时间中,如何更好的分配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时间?
顾久: 电子阅读是基于现代科技所产生的读书方式。目前在中国,电子阅读十分盛行,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我们会在公共场合里看到很多人依然捧着纸质书在阅读。于是我在想,其实电子产品最初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抛弃掉纸质阅读。
鉴于此,我认为中国目前电子阅读盛行的情况,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几乎是跑着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家普遍比较焦虑。比如学生,在家里会被家长压着读书,在学校会被老师逼着读书,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又很快开始焦虑在社会上如何生存——似乎一路都在狂奔。在“一路狂奔”之时,用手机或用电子产品阅读一些小东西,除了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内拓展知识,另外也具有更大的消遣的功能。我认为,这可能是国人喜欢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根本原因。
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实际上可以互为补充:如果想系统的学习知识,或者阅读经典著作,我建议大家认认真真的坐下来,正襟危坐的去读纸质书;如果要拓展信息,特别一些带有新闻性的、转瞬即逝的信息,那么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来的更快一些。我自己也经常看手机,每天早上起来总是要看一看发生什么大事,也在网上关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此外,电子阅读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在思考某个问题时,可以上百度学术或者知网,去搜索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资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推荐爱思想网,在上面可以找到各个派别、各个门类的专家们,比较经典的论文或访谈。
记者: 生活中的琐事缠绕,生命中的求而不得,都让人痛苦。这时,书中的理想世界就提供了“避难所”。读者因为读书而暂时忘却世俗烦忧,让心灵得到了憩息,这实际上也是书籍与读书人的心灵交融。对此,顾久先生一定有独到的见解。
顾久: 人,是三位一体的物种,既有生物意义,也有社会意义,还有精神意义。当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基本都是出于一些现实原因,比如没钱、贷款压力大、孩子读书难、职场不如意等等,有些人会因为想要躲避这些烦恼而去阅读。如果阅读的是一些比较有品位的、能够引导精神、抚慰灵魂的书,那么肯定能起到安抚的作用,但是未必能够解决现实中的种种欲望。所以在我看来,读书的目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探索这个世界,二是定位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如果一直奔走于各种欲望之间,那他就很难安静下来。当我们走进工业社会,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奔腾喧嚣,会变得不断激荡,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快速发展的经济带着往前跑。但这个时期我觉得不会长久持续,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平稳下来,最终都要回归人的生活。
记者: 请谈谈您最近读的一两本书。
顾久: 最近我读了一些与生物学有关的书,有所感悟。什么叫生物?生物就是挣扎着活到性成熟,找到另外一半生下个孩子抚养大。换句话说就是在生命息息相生的链条中间,“你”只是小小的一环。因此,人生在世,有多少钱,当多大的官都不重要,没有意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最终的意义是过了10代20代之后,你的孩子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就说明你的这条分支已经断了,你就是不成功的物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追求的不应该是眼下,而应该是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能够有序发展。所以,我建议大家看淡功名利禄,多追求生命中的平淡从容和诗意。
近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气候灾难和俄乌战争发表了两次讲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原文来读一下,因为这些讲话关乎现实——每一个人都活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链条之中。
记者: 阅读是一生的事。如何培养阅读习惯?如何更好的阅读?
顾久: 我的读书习惯培养来自于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每到星期天都带我们到大十字的新华书店,他自己买书的时候也给我们买上一两本。后来在家里也设立我们孩子自己的书架。我建议所有的家长,都在家里设一个书架,放一些经典著作,时常在孩子面前去翻一翻,为孩子营造一个爱读书的文化氛围。
我父亲读书的时候很严谨,通常会拿支红蓝双色笔,还要拿一把尺子。凡是觉得很精彩的地方,他会划上虚线;觉得很重要,会划实线;非常重要的划两条线,不赞成的或者不理解的,会用蓝色笔做记号。
有时候父亲还会记一些关键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思维导图,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翻一翻,就能大致了解这本书的整个框架。如果还想加强记忆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做读书卡片。我现在读书也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当我看到觉得比较好的一段话,我会在最后一页上边标明这段话所在的页码,即使时间久了淡忘了,只要翻开最后一页,就能够找到当时我注意的内容。
记者: 读书对生活、对人生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顾久: 不看书能不能活?能!不看书也能活,但是不看书就好像没有一个另外的我在审视着现实的我。读书的过程,就是找到一个另外的我来看当下的我。
其实读书这件事发生得很晚。从智人到人,从四足着地到解放双手,大概经历了300万年时间,但是文字的出现最多6000年。如果把300万年和6000年按比例压缩成24小时,那人类有文字,不过是最后几分钟,所以读文字的书籍不代表就有知识和智慧。
生活就是无字书。比如现在依然有一些老年人不识字,但他们依然具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智慧,比如炒菜,比如带孩子。我们认知里那些似乎没有“文化”的人,其实他的知识已经足够让他“活”了。只是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可能活了几十代,但其实只活了一代人,因为每一代人都活得差不多。
记者: 请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顾久: 推荐阅读《万物简史》,这是一部有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普名著,作者以超常的智慧、幽默风趣的笔法,结合有关现代科学的发现,勾勒了自然的演化史和人们认识宇宙、探索万物的科学历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读一本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书。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他本职是医学院生物学教授,但是我读了他这本书后,觉得他可能会是影响当代世界的10个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