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遇乐·落日熔金》 一曲苍凉朴素的爱国绝唱
□ 林坤平
李清照是宋代最杰出的爱国女词人,是中国女性文人中最为闪耀的一位。《永遇乐·落日熔金》是她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伤今追昔之作,全词化俗为雅、朴素清新,以未言哀但哀情溢于言表的方式,抒发了深沉苍凉的故国之思,表达了痛彻心扉的失国之痛,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芒,是一曲苍凉朴素的爱国绝唱。
苍凉:乱世飘零的孤影
陆游有诗云:“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永遇乐》便是李清照流落临安时,感慨今非昔比的“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愁怨愤忧之作。
李清照自幼家境优渥,其父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十八岁时嫁赵明诚,李赵二人在艺术志趣与文学修养等方面情投意合,生活惬意充实。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降临,李清照再也不能安坐书斋、侍弄花草、摆布金石了。在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大背景下,夫妇俩随着逃难洪流跌宕南下。两年后,丈夫病逝。战乱中,她收藏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珍品也丧失殆尽。寓居杭州时,又与张汝舟有过短暂不幸的婚姻。女词人在南渡后经历了重大人生变故,膝下又无子女,晚年孤苦伶仃、凄凉悲惨。
词人避难江南,此时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最令她感到悲凉的是,南宋朝廷早已忘了靖康之耻,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独在异乡为异客,在1150年元宵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里,李清照怀揣着一股刻骨铭心的国破之痛和思乡之情,无限感时伤怀,“谢他酒朋诗侣”,秉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永遇乐》元宵感怀词。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词人浓重的家国之思和身世沉浮的苍凉。上片表述寓居异乡过元宵节的悲凉,下片由上片的写今转为忆昔,以南渡前后过两种元宵节的反差落笔,体现了她个人生活遭遇的巨大变迁,以及对故土的怀念和恢复故国的渴望。词人将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灾难紧紧联结在一起,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反映出国家的危机和历史的沧桑。
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从词人自身的经历来看,李清照经历了前半生的养尊处优到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从生活美满到辗转飘零,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艰难打发岁月。金兵南犯,国破家亡,寄人篱下,词人怎能不为之愁?这个愁,不是娇弱女子的纤细哀愁,而是无限悲痛的沉郁激愤。在这种极端经历中,她“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将思恋故国的情怀化作了苍凉愁绪,把浓烈的家国情怀寄托给了诗词,抒发了深沉的身世之悲、寂寞之境和家国之痛。李清照在写完这首词几年后,便悄然离世了。
朴素:不加粉饰的绚烂
李清照晚年的词作,内容词风、艺术方法上有个突出特点,清人彭孙遹在《金粟词话》中将其概括为“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永遇乐》全词不追求砌丽的藻饰,用语极为平易,无复杂的手法或技巧,蕴藉而不晦涩,深情而出以浅语,有意识地将浅显平易的口语与锤炼工致的书面语交错融合,创造出一种俗中见雅、雅不避俗、雅俗相济的语言风格,给人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南宋文学家张端义从韵律角度对这首词做了具体分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练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两句中皆是浅显易懂的意象,但意境渲染却丰富多样。美景、美人与回忆,构成了一幅生动融洽的图画,映照出词人现实中凄惨的孤影。
事实上,平淡浅近的语言更能展现出词人在艺术创造上的造诣。大凡在生活上遭受过沉重磨难挫折的文人,晚年的艺术风格往往都趋向于平淡自然。苏东坡曾概括出这种文风的变换:“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非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李清照晚年词风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个规律。她在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在不疾不徐的平淡语调中,诉说着苍凉的情感世界。词人在饱经忧患之后,已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头角峥嵘,而转向平易浅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李易安体”。“李易安体”以平易中见清奇,语气平静又不淡漠或压抑,情感一流出旋又收回,一如杜诗抑扬顿挫,克制中内心情感已如暗流涌动,感人肺腑,有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这首词使用了当时大量的接地气的俗语,但其呈现出的高雅意境却非寻常雅语可比。因为,绚烂至极的最终境界总是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丰满的意象和情感。词人在“平淡入调”的炼字炼句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南宋词论家张炎在《词源》中这样例证:“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向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不如向”这句,看似平淡自然,却又横生波澜,以人之欢声笑语,衬我之落寞零落,李清照的满腹辛酸、一腔悲愤,便呼之欲出了。
爱国:悲愤忧国的绝唱
李清照受到“诗庄词媚”传统的影响,其词的社会政治功能含蓄委婉,但词中的爱国情思仍清晰可辨。《永遇乐》即是通过个人身世际遇的抒写,赋予了这首词以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了国家沦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精神创伤,表达了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不满。全词温婉清幽,出语清淡,用情极苦,堪称惊才绝艳、心怀家国的悲歌绝唱。
《永遇乐》表面是讲过元宵节,实际是在说时政;看似婉约,实际上将感愤时事的情思潜藏在幽深的意境和悲苦的情调里,寄寓着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和以身报国的期盼。相对于柳永《雨霖霖》那种描写花前月下的作品的情怀境界,李清照以生命与灵性书写的去国怀乡、离人盼归和国破之恨的浓重隐忧,实际是事关社稷江山、民生福祉和时代走向的重大问题,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越了闺阁情愁。我们透过纸背细心体味,便能领悟到这位词人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社会大氛围中,对“来相召、香车宝马”的上层作出坚决否定的凛然正气。
非斯人而不足以为此文。“诗言志,词言情”,说的是诗词品格与作者人格相辉映。诗词书写的是作者主体意识的活动,其志向高低与诗歌优劣密切相关。这就是“文如其人”。李清照虽是一位被社会政治排斥在外的女性,却有着不让须眉的政治远见:一句“次第岂无风雨”,就一眼洞穿小朝廷的投降卖国和侵略者的胃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本性。
李清照忧患民族的担当,足以睥睨天下,让人肃然起敬。虽然她没有辛弃疾、陆游等词人经历过的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其词作是由个人不幸引发失国之痛的感怀,但这种个人遭际的悲叹已超越了个人身世之悲,反映出战乱年代百姓和社会的共同哀愁以及对统治者“不知亡国恨”的愤恨。
因而《永遇乐》中沉淀着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国情感,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辛弃疾、刘辰翁等词人都曾为之涕下而起效“李易安体”,或心心相惜、推崇备至,或依声填词、玄续忠魂。
时代的苦难与个人命运的不幸,让一个闺房词人冲破了花间闺怨词的樊篱,在逆境中成为宋朝第一女词人。这位传奇女子的横空出世,撑起了一个时代的风流往事,也彰显了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明人杨慎评价李清照言:“使在衣冠,当与琴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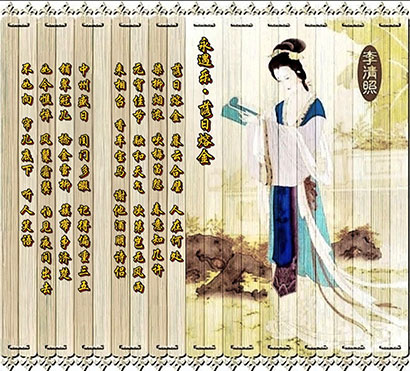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