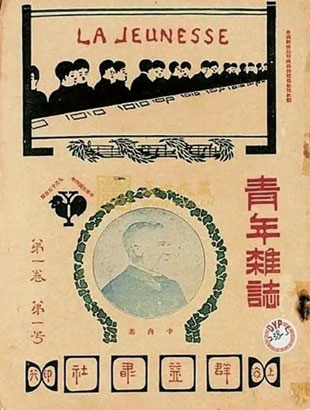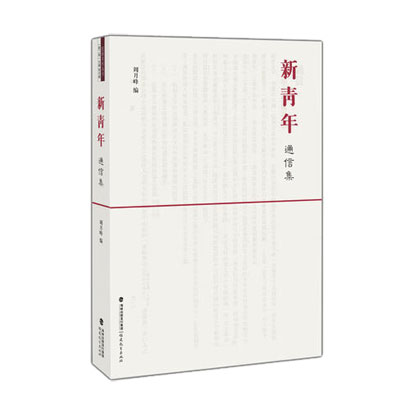《新青年》在贵州的传播
——《新青年通信集》札记
□罗晓东
一
一日,收到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孙汉生先生给我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全是精神食粮,有《君子儒梅光迪》《书淫艳异录(甲编、乙编上下册)》《<新青年>通信集》《<甲寅>通信集》,共计五本。为不辜负汉生先生的美意,我随即将所有书的目录翻阅一遍,发现许多文章都很有价值、有意义,于是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华中师大周月峰博士所编《<新青年>通信集》一书,搜集整理《新青年》来往通信702篇,凡70多万字,都是一百余年前“五四”前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诸位大家与《新青年》编辑部的来往通信,比如众所周知的蔡元培、钱玄同、胡适、林语堂、刘半农、陈望道、梁漱溟、周作人、张东荪、罗国杰等等,其中《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致记者》引起我的极大注意,该信刊发于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期,作者是贵阳的一位青年读者。其究竟为何人,是否名家大家,现在无法考究。《新青年》杂志能够刊发来自贵阳的化名作者来信,除了信件的质量原因外,我想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贵州的新文化、新思潮引起了《新青年》杂志的注意。在我看来,这是《新青年》杂志比较特殊的一份通信。遂细读该文,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便以“键盘”记之,算作文史资料或读书札记,予以保存。其原文如下:
记者足下:
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入政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
愚以为今后大志,当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盖现政府之不可谏、不足责久矣,乃必欲哓哓不已,不唯无益,徒贾祸耳。若专培养后进之知识,俾其积理渐厚,较为有裨实际,亦符大志斯作之本心。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一卷第一号“通信栏”答王、庸二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且足下云:“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尤为真确透辟。然则无益之批评,又何取耶?又青年求学之时,似不宜以政谈引起其嚣张之恶习,而真确之学理,又不可不急为阐明,以深树日后不拔之基。诚恐大志恶夫政象之不良,著论力辟,遭厄于大力者,强令停刊,则吾辈青年之粮饷,或将再断矣。用将此意进于左右,祈垂察焉。
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上
由该信可知,1916年9月,贵州读者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上”之名义,给《新青年》写信,并得到《新青年》采用并刊发出来,说明《新青年》已在贵州得到传播,也可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在贵州传播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
20世纪早期,世界风云激荡,各种思想潮流在中华大地涌动撞击,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起来,中国进入一个思想大解放、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一面当时思想解放的旗帜。从1917年到1922年这七年期间,《新青年》杂志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哺育了一代青年,可谓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上伟绩卓著,彪炳千秋。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够直接介入并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走向,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新青年》的传播过程中,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思想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广为人知;而在交通闭塞、社会沉闷、文化教育落后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在贵州的传播情况,长久以来都乏人问津,这反而更值得我们现在加以关注和研究。而这封来自一位贵州青年读者的来信就弥足珍贵了。
贵州学者对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老师——熊宗仁先生,他是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史学会原会长、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他于1983年在《西南军阀史研究》第3辑上发表论文《兴父系军阀与贵州五四运动》;1986年又正式出版了《五四运动在贵州》一书;1988年在《近代史资料》第72期发表《少年贵州会资料选》;1989年在《贵州青运史料》第一期发表《五四前后的贵州青年运动》、在《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让五四传统在深化改革中发扬光大》等文章。贵州其他专家学者还有范同寿、史继忠等先生。从他们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提出“贵州缺乏新文化运动深厚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一百年前的新思潮对贵州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20世纪初,由于群山环绕,交通阻滞,加之封建割据军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新青年》杂志在贵州传播、发行的情况并不理想。那时传播方式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就是在杂志本身的传播,间接就是口头的传播。具体情况如下: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间过去3年多之后,即1918年初,贵州的群明社才开始发行《新青年》。“群明社”由贵阳人蔡岳创办,其家有“蔡恒泰”商号,经营绸缎,后增加书籍、百货等业务。蔡岳参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自费留学日本,著有《黔学之础》一书。黄齐生、王若飞曾在群明社做事。后王若飞赴法勤工俭学,蔡岳对其予以资助。可见蔡岳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开放的进步人士。
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2年7月1日九卷六号的出版,西部地区约有11人,累计在《新青年》上刊发文章(包括通信、诗歌、译作)27篇,其中,四川有8人,陕西、云南、贵州各1人(贵州人吴葆光在三卷五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方法》),而在这11人中,无一例外都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或海外求学时,就受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中国文学网)。
为回应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创刊3年之后,即1918年,贵州成立了“少年贵州会”,贵州先进青年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在全省建立77个分支机构,主要进行文化活动,开办外文学习班,举办各种讲座,开展体育、新戏、音乐等活动,目的是为了“振作朝气”,打破死气沉沉的“暮气”,培养“少年精神”,大声疾呼“警醒夜郎”,开启贵州一代新风。
在“少年贵州会”推动下,话剧运动在贵州兴起,贵阳戏剧舞台出现新气象,比如达德学校演出的话剧,使人耳目一新。以贵州各界发起的“救国储金运动”为背景,贵阳川剧班排演新川剧《乞丐储金》,上演捐钱给救国储金的感人故事。贵阳话剧运动延续至抗战时期进入高潮,在全国占重要一席。
与此同时,《新青年》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在贵州文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带动了贵州文学的迅速发展,比如贵州本土作家蹇先艾以《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揭示出西南山区的闭塞、愚昧与底层人民的苦难,同时也体现出了“老远的贵州”独特的乡间习俗。
在新思潮启迪下,贵州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大山,到日本留学,到欧州勤工俭学,到北京、上海求学,有的成为共产党的杰出人物,有的成为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
综上观之,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在贵州的传播虽然相对较晚,但为“五四运动”在贵州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为贵州社会变革掀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