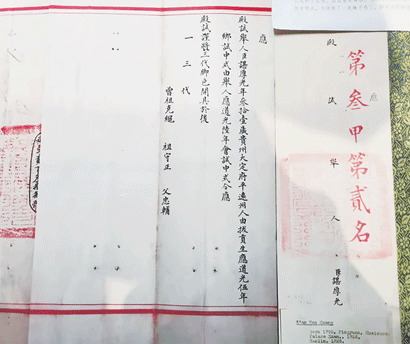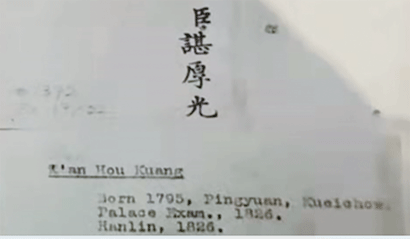明清时期贵州文教日盛的见证
——从清代贵州籍进士谌厚光考卷说起
□文/图 张春来
早在2015年,贵州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女士开始知晓并接触到该校图书馆馆藏近500份珍贵的清代科考考卷。2016年经过其本人与时任中国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认真拣选整理,共统计出该批清代科考考卷有文殿试考卷219份;翰林馆选/翰林朝考考卷82份;武殿试考卷6份;国子监肄业考卷32份;吏部拣送官员考卷49份;书院考卷97份;秀文选制(笔者注:相当于优秀文章选编)10份。经陈肃女士考证,该批考卷是目前已知海外最大藏量清代考卷,时间跨度从顺治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包含了112次殿试中的63次考卷,考生籍贯分属清政府下辖的全部18个行省,考生来源广泛,堪称研究清朝社会制度、文化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让陈肃女士惊喜与意外的是,这批种类丰富、价值不可低估的科考考卷中,贵州籍进士考卷竟然占比最大,足足有67份之多,明显多于位列其次的40份江西籍进士考卷。
在专注于贵州科举历史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厐思纯先生看来,“煌煌”67份清代贵州籍进士考卷无疑为明清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一说添上了分量十足的脚注。2018年,为一睹真容,厐思纯先生专门远赴大洋彼岸亲自考察,欣喜地发现在67份贵州籍进士考卷中,有来自贵阳著名文化世家、号称”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何氏家族的何鼎;有贵州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晚清名臣李端棻叔父、顺天府府尹李朝仪之子李端榘;有贵州籍清代大臣、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之子黄国瑾;有蜚声省内外的遵义沙滩文化创始人黎安理重孙黎尹融等等。除了难得一见的殿试文章,每份考卷的扉页都注明了应试者个人简历以及本人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等详细信息,厐思纯先生情不自禁感慨“这为研究贵州科举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此外,考卷揭示的最“年少”进士安顺府人杨恩元(时年17岁),最“年长”进士贵阳府人尹祖依(时年46岁),无不令人感叹于天资各异、时运殊同之人在科考路上的不同际遇。
67份考卷,67位贵州籍进士,他们中有的声名显达,有的籍籍无名。并不是每一个名字都会被后人铭记,也不一定会被学者不约而同提及。谌厚光就是其中被“忽略”甚或“无视”的一位。这或许多少和他的出身有关,与以上或出身名宦之家,或成长于著名文化世家的“考生”有所不同,谌厚光的出身相对普通很多。据道光《平远州志》记载,其父谌忠辅为廪生,也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秀才,功名不显。但对于他的家乡,清代贵州平远州(今织金县)而言,谌厚光是一位无法被忽略,也不该被无视之人。
谌厚光,字蕴山,号葆初,贵州平远州人。嘉庆十八年(1813)选拔贡,朝考一等,以七品京官用签分刑部,升候补主事。道光六年(1826)中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继授检讨,后出任山西大同知府。致仕回乡后主修《平远州志》并作序,其平远州府邸被称大同府,俗称大府头。
明清以降,贵州文教日盛,诞生了号称“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这其中,地处黔西北的贵州织金县(清为平远州)一共走出来十二位大清进士,其中有四位翰林。首当其冲的便是晚清名臣四川总督丁宝桢,任翰林院编修。其次是清初贵州著名诗人,出身诗人世家的翰林院检讨潘淳,之后是嘉庆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广西南宁府知府何珣。最后就是本文主人公谌厚光,道光年间任翰林院检讨。翰林一般由进士选拔而来,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视为通达仕途的清贵之选,乃进士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如此看来,在贵州“七百进士”中能够脱颖而出,荣登“翰林”之列,谌厚光的能力与素养是足够优秀的。
正如前文所述,即使位居科举考试的塔尖,也并不是每一位进士都能被浓墨重彩地书写。时至今日,笔者通过百度百科查到的谌厚光相关介绍也只是以下寥寥数语而已:“谌厚光(1821-1850):清道光六年丙戌科三甲进士(朱昌颐榜),勤奋有为,(大同府)王河涨水时组织修堤护城,平市商限息,调剂其盈虚缓急,定为每年三限,商民称信。”另《山西通志》有载:“(谌厚光)德行谦谨,重士爱民,奋励有为,以兴利除弊为己任,王河涨发,啮及城垣,修堤护之。平市商限息,调剂其盈虚缓急,定为每年三限,商民称便,到今相仍。”
上述介绍虽大体符合史实,但谌厚光的出生日期存在明显错误。若是出生于1821年的话,那他岂不是6岁就中了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进士?之前的嘉庆十八年(1813)选拔贡更是“无稽之谈”了,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但谌厚光究竟生于何年,这个问题不仅一直困扰着笔者,也困扰着他的家乡。最近一两年声名鹊起的贵州织金平远古镇有一处“名贤园”,园中有一组以丁宝桢为首的织金历史名人雕像群,其中就有谌厚光的雕像。令人遗憾的是,雕像所附简介虽纠正了“生于1821年”的谬误,但也只能无奈地标注为“谌厚光(?-1850年)”。据此可知,有关方面虽做到了尽量谨慎以免“授人话柄”,但却不知去哪里、如何知道其真实的出生纪年。
幸运的是,笔者一位中学同学的一次“无心之举”就此解开了这一“历史谜题”。该同学在去往中国传统村落、贵州安顺市阿歪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无意中在该村新近落成不久的“山骨图书博物馆”展厅看到了部分前述美国馆藏贵州籍进士殿试考卷,其中就有谌厚光之试卷。出于老乡的本能与对家乡先贤的敬仰,这位同学当即就把卷首拍照保存下来,并分享给了素来对地方文史有着浓厚兴趣的笔者。待笔者拿到照片后仔细端详,可见数行端正清秀的楷书写道:
应
第三甲 第二名
殿试 举人 臣谌厚光
殿试举人臣谌厚光年三十一岁 贵州大定府平远州人 由拔贡生应道光五年乡试中式 由举人应道光六年会试中式 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与后
曾祖克绳 祖父守正 父忠辅
其中第三行“臣谌厚光”下方有几行很容易被忽视的英文注释:
Chan Hou Kuang Born 1795,Pingyuan,Kweichow. Palace Exam,1826.Hanlin,1826。
出于在高校教授英语的职业敏感,我立刻意识到这几行英文注释的重要性。很明显,学过英语以及对威妥玛式拼音有所了解的读者朋友不难解读出注释的中文含义为:“谌厚光(Chan Hou Kuang),1795年生,贵州(Kweichow)平远人。1826年中进士,同年选翰林。”再与谌厚光考卷本人简介中“臣谌厚光,年三十一岁”两相对照,不难推断出1826年应殿试时正值31岁的谌厚光正是生于1795年。这么一来,一道困扰人们多年的历史谜题终于迎刃而解!(笔者注:威妥玛式拼音法,简称威氏拼音,1867年由英国人威妥玛等人合编而成。威氏拼音在1958年新中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广泛被用于中国人名、地名注音,影响较大。后逐渐废止。)
据道光《平远州志》记载,从山西大同府知府任上致仕归乡的谌厚光并没有闲下来。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时任知州及平远一众乡绅的恳请下,虽自称“余自维宦游阅三十载,乡间所闻,半涉生疏,且制中抱恙,笔砚尘封,再三辞不获命”,谌厚光还是应承了主持纂修州志的艰巨任务,“与同学诸友,互操铅錾,各分目而编辑之……不数月而竣事。”期间,谌厚光抱病亲自作序,并撰写《嘉庆二年平苗纪事》等文。以其为首,在数十位织金籍举人、贡生、诸生以及乡绅的“众人拾柴”下,研究织金古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地方历史文献,清代地方志孤本道光《平远州志》得以问世。
除了抱病主持州志纂修,据刘玉明《织金老城纪事》一书考证,谌厚光不仅在任职期间捐资修建织金杨泗将军庙和东山读书楼,还在返乡后出任彼时的平远州凤西书院主讲。告老还乡后,谌厚光在今天的织金县城大府头广场处修建了自己的府邸—太史第,因形制与大同府官邸相似,又被称为“大同府”。随着时光的变迁,“大同府”演变为了贵州织金本土知名度最大,在每一位织金人回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大府头”。
《平远州志》成书后不到三年即公元1850年,为织金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莫大贡献的谌厚光与世长辞,享年56岁。与封疆大吏、平远同乡丁宝桢相比,谌厚光只是清政府万千普通中级官员中的一位,两者的历史文化影响力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上可知,谌厚光回乡后的作为深深地“嵌入”了织金本地历史,在地方百姓的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不得不说,与“高大上”的丁宝桢相比,谌厚光的形象或许更加的亲和与具体。如我所想,历史不应该只是围着所谓的“大人物”打转,适当地发掘与书写类似谌厚光等“小人物”的相关事迹,如此的历史兴许才是有温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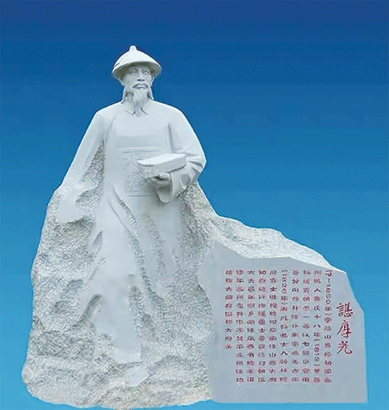
谌厚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