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原名萧秉乾,是近代中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翻译家,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自称“未带地图的旅人”。他1910年生于北京,童年时期在贫苦中度过,靠做童工赚钱读书,使他对底层生活有着深刻的感受,也培养了他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萧乾是贵州女婿,夫人文洁若是著名翻译家。文家是贵阳的世家,文洁若的父亲文宗淑民国时期在驻日使馆任职20年,母亲万佩兰也出身贵阳名门。舅万勉之是贵州第一代官派留学生,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小舅万徐如为贵州抗日名将。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萧乾也被列入贵州文化名人一起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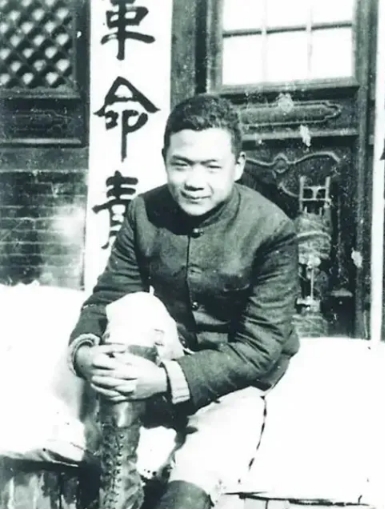
青年萧乾
1935年7月,萧乾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接编该报副刊《小公园》。但此时《小公园》不能与时俱进,已落伍于时代,仿佛“只是编给那些提笼架鸟的老头们看的”,与时代严重脱节。萧乾本身是个文学青年,他的一部短篇小说《蚕》,曾获得才女林徽因的高度赞赏,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萧乾的小说既有中国文学传统诗篇般的精巧构思,又广泛吸取了西方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意识流等的运用使其作品构思精巧、比喻独特,既具民族特色,也有现代色彩。其散文清雅俏皮,杂文铿锵有力,在当时与沈从文并称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小公园》已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在《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支持下,萧乾对《小公园》进行了改版,使之在内容上耳目一新,与时代合拍。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由一个综合性副刊变为一个纯文艺性副刊,可以说在当时与杨振声、沈从文等编辑的《文艺副刊》几乎并驾齐驱。
从当年9月1日起,《文艺副刊》和改版后的《小公园》合并为《文艺》,由萧乾担任主编,每周一、三、五出版。《文艺》一般刊登一些短小的文章,开设各种专栏,但仍保持原《小公园》的基本面貌,周日出版的主要是名人作品,辟为特刊,如“诗歌特刊”“艺术特刊”“翻译特刊”“教育特刊”等等,又基本上保持原《文艺副刊》的特色。
《文艺》的出版,不仅一改《小公园》那种老气横秋的面貌,还赋予了较强的时代气息,不仅发表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刊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的处女作,因此很快声名鹊起,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不仅是《大公报》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文艺界一件值得纪念的盛事。这一时期的《文艺》,不仅拥有全国文艺副刊中最广泛的作者群,而且被誉为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的“文学摇篮”。
当时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相当一部分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率先发表,得以脱颖而出。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因此,《大公报》副刊,与《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论文和新闻通讯一道,被中国新闻史学家评为“当时新闻界四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大公报》上海版被迫压缩版面,《文艺》在裁撤之列。这样一来,作为该刊主编的萧乾因此失业而丢了饭碗,只得和其他报馆同仁一样,拿着报馆发给的3个月薪水自谋生路。
萧乾离开上海后,经香港、广州,于同年9月到了武汉。此时,《大公报》汉口版已经创刊,而《战线》副刊已由陈纪滢主持。萧乾就职无望,只好辗转贵阳,最后落脚昆明,另谋出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开始了滇缅公路的修筑。南京沦陷后,中国海岸线被日军日渐封锁,所有军需物资必须经由越南、缅甸入境,云南边陲之地也变为连接外援的咽喉要道。云南爱国民主人士缪云台作为特使前往缅甸仰光,与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公路修筑事宜。最终议定,由缅方完成从缅甸美苗到中国畹町段的修筑。这条公路的意义,按缪云台所言:“无须多言,民族危亡,它是我们的生命线!”萧乾到昆明后,即对滇缅公路进行实地采访,发表了纪实通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这时,《大公报》文学编辑杨振声、沈从文、萧乾重聚昆明,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不久,胡政之来信告诉萧乾,说《文艺》副刊曾在社会上产生过较积极的影响,许多读者要求复刊,请他在昆明遥编,在汉口版刊行。同年10月3日,《文艺》在《大公报》汉口版面世。汉口版上的《文艺》为周刊,至1938年3月6日为止,共出版23期。
1938年夏天,萧乾突然收到胡政之电汇来的旅费和一封信。信中对上海遣散一事深表歉疚,并说今后再不能使同仁星散了,同时希望萧乾立即到香港,为大公报港馆重整旗鼓。于是,萧乾于8月初到了香港,参加港馆恢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筹备工作。
淞沪会战后,《大公报》香港版正式创刊,《文艺》也随之复刊。如果说《文艺》副刊在创办之初即已赢得读者的赞誉,那么,它在成为《大公报》香港版的主要副刊后,更是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因为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它都表现出了鲜明的进步性和战斗性。
1938年9月17日,日军下达了对广州的作战指令,随后广州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全部沦陷,华中全面受敌,香港正式进入至暗时刻。作为战略要地的香港,被日本觊觎已久,故《文艺》在香港复刊,无疑是将阵地搬上前沿。
《文艺》在香港复刊后,在战争局势下,作者四散飘零,稿件难求,稿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从“编辑”。萧乾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之前的作者。后来,《文艺》与西南联大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和互动。
与此同时,萧乾在副刊上刊出题为《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向过去经常为《文艺》撰稿的作家朋友发出呼唤:“两周前,我由西南一座山城来到了香港,今后,我将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住址了。同时,三年来你们所爱护支持的那个刊物——《文艺》,已于‘八一三’周年日在港版大公报上复刊了,想来必是你们所乐闻的罢……这刊物在太平年月,它载的是坚实健康作品,在战时,它自然也得积极参与全国文化的总动员,展示新的姿态……但这只是我的愿望。实现这愿望,还得靠你们和各地的朋友们。同时,我也在盼着你们的来信。”萧乾在这里,对《文艺》今后的发展,明确表示了两点:一是鉴于抗战的新形势,准备引导《文艺》参加全国文化抗战的行列,并在抗战宣传中展示其新的姿态;二是希望《文艺》的老作者们对此予以理解,予以支持。
在此期间,杨振声和沈从文鼓励萧乾:有西南联大在,稿件不用愁。杨振声是西南联大秘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沈从文次年也进了西南联大。沈从文还拿出长篇散文《湘西》供萧乾应急。很快萧乾《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也得到了老友严文井的回应。1938年10月12日,萧乾在《文艺》上发表了严文井从陕北寄来的这封信。信中主要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情况,还谈到住窑洞、吃小米的特别滋味。该信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地作家也纷纷来信,诸如姚雪垠、吴伯箫、丁玲、刘白羽等名家大腕,可谓盛况空前。
为了及时刊登来稿,萧乾在《文艺》上专辟“作家行踪”一栏,借信件的报道,让读者了解到活跃在抗战各条战线的大量作家的近况,其中尤以延安作家居多。与此同时,一些流亡到大后方的作者朋友也陆续来信与萧乾取得联系。萧乾与各地作家,尤其是延安方面的作家取得联系后,为《文艺》副刊“展示新的姿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文艺》在《大公报》香港版上复刊后的第一个任务——找寻作者,就此顺利完成。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来自延安的作品在《文艺》上发表的共计44篇。这些反映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战斗性强,还不乏上乘之作。《文艺》刊登这些“投笔从戎”的作家寄来的文章,充分展示了第一个新姿态。
《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副刊所展示的第二个姿态,就是创办《文艺》的综合版。关于创办综合版的原因,萧乾曾作过解释说:“报纸副刊的读者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的专家肯动手写点大众化的东西,它的前途必是无限量。”无疑就是要充分发挥副刊读者面广的优势,利用副刊加强对民众的舆论引导和胜利信心的注入,加强它的可读性和战斗性。
有了杨振声和沈从文的帮助,西南联大的稿源也相当丰富。林蒲的长篇报告文学《湘西行》,在《文艺》连载了3个多月。对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沿途做记录,介绍旅途见闻,反映湘西民气。作品围绕“抗战民气”着墨,揭示民众参战的勇气及对胜利的信心,是鼓舞民心士气的“抗战文学”。在写沦陷区的作品中,小说尤为突出。辛代的《九月的风》描写“九一八”事变中“北大营”中国军队的情况,《弟弟》揭示沦陷区孩子的悲苦生活。流金《母亲》描写炮火中母亲送走女儿的生离死别,《八年》表达在日军占领下对故乡的怀念。祖文的《端午节》记述一个青年逃离日据区的心理和行动。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国民坚韧顽强、不怕牺牲、勇于反抗、夺取胜利的民族气节,给人以光明与胜利的希望。写国统区的作品内容尤为丰富、文体多种。散文如向薏的《在南岳》记述长沙临大的生活,王佐良的《公路礼赞》颂扬大后方的交通建设。诗歌如穆旦的《漫漫长夜》描写民众忍辱负重支持抗战的热情。当后方遭到轰炸,作家便及时予以曝光谴责:陈时的散文《大学园地》描述日机轰炸云南大学的惨象,揭露侵略者对人类文化的摧毁暴行;向薏的小说《许婆》则通过两个儿子的死难和许婆精神失常的描写,揭示大轰炸对普通家庭的摧毁和打击。这些作品以悲剧的力量,激发读者的反抗精神。王佐良的《老》写武汉沦陷后,日本兵逼迫商会的老头子组织开市,却想不到青年人正在策划对日军的毁灭性打击。该作品给人以鼓舞和希望,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二戆子》是林蒲的一个作品集子,全是抗战文字。其中《二戆子》和《人》最为优秀。小说《二戆子》写一支地方队伍伏击敌人的故事。指挥员采用靠近才打的战法,11人歼灭日本兵二三十个,让人感到畅快淋漓。该文虽未刊载于《文艺》上,但《文艺》对其同名集子作了介绍:“林蒲先生这本《二戆子》是从血的生活中收获而来的。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忧郁,反之,是气魄豪壮,行文刚健的。……很有真实动人的力量。”报告文学《人》把人们的目光带到国际视野。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人达拉毅然改国籍为“中国”,得以报名参加“华侨机工”,驾驶汽车在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颂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援助的道义。《文艺》在港期间,发表了西南联大24位作者108篇作品,分208次刊出。这一数字体现了萧乾与该校的深情厚谊,以及《文艺》的办刊方针。
《文艺》综合版于每周日刊行。在这一版上,凡是具有鼓舞抗战士气的文章,无论题材如何都可以发表,而揭露日本政治黑暗、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作品,更是综合版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下村千秋撰著、高行翻译的《狐狸精附了体——战时日本童工的剪影》(发表于1939年3月11日),《死亡线上战栗着的日本大学生》(发表于1939年4月1日)等,这些反战作品在《文艺》综合版上发表后,在当时曾引起过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之,为了把《文艺》办成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萧乾可谓苦心孤诣,义无反顾,他八方征稿,四面出击,使《文艺》成了抗战的有力武器。
萧乾被派往欧洲后,继任的《文艺》编辑杨刚延续同西南联大的合作与抗战方向。1941年11月香港危急时,《大公报》撤回桂林出版,《文艺》的合作方与方向仍未改变。抗战后期,萧乾放弃了剑桥大学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奔忙于西欧战场上的中国记者之一。他向世界报道欧洲战场情况,也为国内国共两党提供了十分及时和重要的欧洲战场信息。因此萧乾及其《文艺》理应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让后人铭记。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2期」
文史天地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承办:文史天地 联系电话:0851-86827135 0851-86813033 邮箱:wstd3282@sina.com
黔ICP备17008417号-1  贵公网安备 52010302000499号 建议使用1920×1080分辨率 IE9.0以上版本浏览器
贵公网安备 52010302000499号 建议使用1920×1080分辨率 IE9.0以上版本浏览器
技术支持:泰得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