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诗心写乌当
——《家住乌当》序
□李 裴
“乌当在哪里?”“哪里是乌当?”朋友问我,我问朋友。问题似不复杂,要妥当回答,却并不简单。2021年“大雪”时节,一众文友,如白庚胜、叶延滨、王久辛、李发模、安琪……,齐聚乌当,隆重举行“诗意纪实·乡村振兴”之“康养胜境·活力乌当”全国名家采风活动。王鸣明先生笔端抒情,谓此乃“赏心快事·恰情雅事,仲冬时节寒意虽浓,文坛盛会却热情涌动”。采风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诗人们行笔于采风中,“乌当之问”大约总是萦绕于脑际,并往往深夜叩问于主人。
这次辛丑牛年冬月的采风,名家们在乌当沉浸体验、边走边看边听,提笔或敲键写作,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活力乌当》诗文集。大多精彩之作,行健载物,可观可感,灵动鲜活,妙语解颐,这部诗文集也许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乌当、了解乌当、走进乌当。李发模老师怎样看乌当?他的言辞是肯切的:“乌当之乌,在天是金鸟,即太阳。乌当之当,在地是指人的担当。乌当之名与布依族语‘美好家园’对应,即宜居、宜业、宜游之地。这儿有红的历史,绿的生态,更有汉族、布依族、苗族等33个民族的活力。这是一方康养胜境,有温泉洗心、空气清肺,能活力健身。”不愧见多识广,功力老到,这段描述含藉着广博的“天地人”要素,怎么看都把乌当“立”了起来。
《活力乌当》里的文字,可称之为是乌当的形象代言,是乌当内在活力的热情喷涌,是充满活力和饱含情感的。白庚胜先生直接了当点赞:“错把乌当当苏杭/天上人间。”王久辛先生则诗句灵动:“那个小碎花连衣裙在蜡染小店里招展/想象着他的她穿上会不会飞起来?/至少,她的欢喜会飞起来/她明眸里面的光,会飞起来/虽然她有点矜持/但她的心儿,一定会飞起来……”是在说买连衣裙吗?是的。但,更在说乌当靓丽美好的情愫。
史实地、诗意地、综合系统地“描绘抒写”,展现具有文化鲜活性的乌当,把乌当锚定在“文史诗”之中,是这部采风作品内容的一个坚实蕴藉和文字表现的一个鲜明特色,更是留给诗人杨杰的一个“大课题”。前两天,收到杨杰微来的《家住乌当》长诗稿的电子版,甚喜,掐指一算,诗人杨杰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为了这近5000行串珠成链的诗句,查阅资料,研究史实,实地走访,浸润体验,始终满怀热情和激情,星星月亮,砥砺前行。读着富有张力的句子,领会其整体意韵,放眼于时代的风采,顿然对杨云龙诗友的“小语(杨杰)是创作大背景、高难度、开风气的长诗先锋。……既体现了工作上的真情实意,又丰富了乌当文旅的内涵,更充实了活力乌当本土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评论,深表赞同。
“乌当”在杨杰的长诗《家住乌当》里,历史根源的线索是清晰的,我们读到“‘水东’千年文化帖、新堡‘屯’有明朝那些事儿、水田庋藏‘唐家顶子’及其他,温泉城念想、乡愁百宜、方聪与一座纸浆博物馆的艺术普世”,文化承续、人文景象历历在目;读到“偏坡醉美半日阳光、香纸沟的竹海溪流与碾坊、枫叶谷那枫叶红”,感受到乌当地理上的温馨和独具旅游价值的自然景观,恰如“山影争着来陪唱,松涛乐意来伴舞”,人与自然之和谐即在此景此情之中;读到“山也,坡里小苑读书季、露营羊昌花海与轻奢偶遇、品王岗,很庖汤”,满目是烟火乡愁的浓烈,不禁深陷其中,耳边居然是“一把野葱在田埂上漾出笑声”,深藏这份乡愁的怀念和珍惜,深含乡情情感的丰富、具体和细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读到“黄连村的红色诗签、李四光之光、‘三线’记忆与信箱里的青春岁月”,这鲜明的红色记忆,谁能不为之动容!
“乌当”在长诗里,所涉“对象”的内容,如果是一般“叙述”“记录”“记载” “资料转写”……那一定是味同嚼蜡、索然无趣了。而在诗人杨杰笔下,那些字句“活蹦乱跳”,紧紧联系在一个诗歌表达的整体中,收放自如地在总体形象空间里实现其艺术审美的“拿捏”,用一种诗意审美的状态来呈现“这一个”“作品中的乌当”“艺术想象中的乌当”,却又把想象风筝的牵线牢牢掌握在“生活现实”“时代变幻”之中,以文学思想、哲学思辨支撑起其艺术形象的生动具体和鲜明丰满,给作品灌注了令人读之击节的艺术生命力。
可以说,杨杰长诗里的“乌当”,是“乌当人”安身之所,独属于此地的历史地理,赋予这里的人一种属于此地的文化气质,成其为安心之所。因其身所居,心所宁,故此而安魂。这安魂的表现,在当下现实生活看来,似乎可以用“乡愁”二字表述之。于此,可见王鸣明先生“以史厚文”“以文润心”之论述的内涵该是多么深厚,细品“泉城五韵”演绎出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动人乡韵,无不透射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浓浓乡愁。而何京先生的叙述,字字敲击着读者的心扉:在乌当乡间的日子,“小住些时日,晨起,院里移步,见山间流岚把眼前的原野笼罩,只有山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居所小屋宛如仙界楼阁,思若缕,接广宇”。写到此,何京先生妙语惊人:“入夜,露台上举目仰望,明月高挂,清辉撒布,村落和田野归于静寂,心与月,同澄澈。”这种心月同澄的至境,非至人不能至。
从时代纪实的角度看长诗《家住乌当》,可归之于乡村振兴题材类的创作,贵州作家在这方面的抱团创作对杨杰来说是有益的。历时数年,贵州与此相关的长诗创作颇有成效,足可自豪。比如,“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就有20部,“时代大英雄”长诗也创作出版了20部,“脱贫攻坚”诗集13部,“乡村振兴”诗集也有6部。放眼望,贵州作家仍在努力,他们热情不减,奋力而为。阅读这一系列长诗作品,总的感觉是历史是现实厚重而富有文化生活气质的。窃以为,至少,对于乡村振兴之文化振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已经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文化助推的作用。目前,我们仍然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长诗被创作出来,在这点上,我始终信心满满。
史识根脉,诗心空灵,“实”之如沃壤,“虚”之如鲜花,虚实之间构建了长诗《家住乌当》。这是诗人自身的创作天赋加持,更是诗人的足下功夫和对文献资料的深耕细作、提取养分,终至于诗句、诗意灿然(据杨杰记录,此长诗已经修改15次)。畅快地大声读一读,“一条河啊,或每一条河/都有太多史事/那是历史的长河//往事是江河在做笔录/见证‘水东’这条没有江水的河流/慢慢流进乌当,写经典无数”;“渔洞峡供着‘水东’肖像/意境是每一滴浪花每一个涟漪/潋滟成诗一样的火把/点燃夜郎,点燃磅礴乌蒙”;“‘山也’和‘坡里小院’的月光会转弯/有永不枯竭的梦想”;“老乡说从羊皮寨到黄连全是山路/很险。险/才是红军走过的路/教人望而却步的胆怯/方为红色之道啊”!
这应该是一种文化创造,《家住乌当》提供了一个“诗人视角”,可以让人从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当下的乌当,进而更好地更深层次地去理解乌当,并对乌当的未来愿景充满热情洋溢的想象和期冀。《家住乌当》或许能别样地开剥出一个想象而奋进的新的视角和空间,也可能提升一种历史的自信、文化的自信,在回溯赓续历史文脉中,激扬谱写当代华章。展读吟诵《家住乌当》,那些燃烧的句子不难让人体会这诗的空间里,对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信心,主旋律嘹亮高昂、热情饱满,这也正呼应着王鸣明先生所言:“黔中风光无限好,且看乌当正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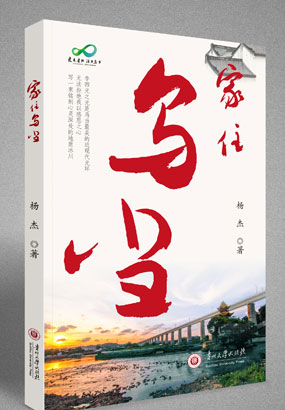
《家住乌当》
杨 杰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